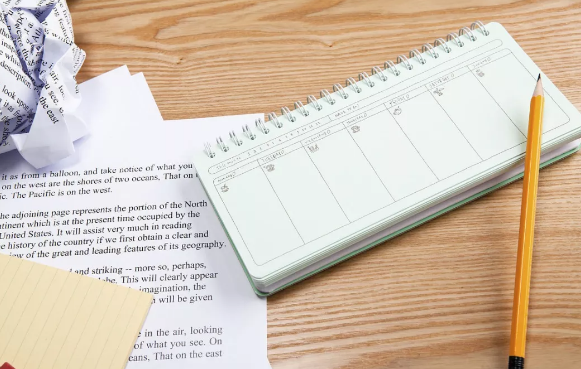休了一年多产假,又到了该回去上班的时候了。说实话,能从一天无休无止的奶瓶和尿片中暂时解脱出来,和外面的世界重新取得联系,也是我一直以来所盼望的。等待我的是一个个工作offer的电话,和一个个不同的学校,不同科目和不认识的学生。换句话说,我的工作没有稳定感,因为我是一个“候补老师”(supply teacher)。
说到“候补”,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在球场上坐冷板凳的替补队员,等队友被罚了、受伤了、或者挺不住了,才有一个上场的机会。“候补老师”,顾名思义,和替补队员差不多,不同的是,我们替补的是其他老师,我们的“战场”在学校。
又要“上战场”了,我不由得翻开了自己放产假前的“候补工作日志”。看着那上面一个个我去过的学校和班级,仍然有些不敢相信我居然从那么多的学校、那么多“任务”当中存活了下来。
第一次听说有人用Survive(生存)这个词形容我们这个工作,是有一次在一间高中做候补的时候,当时午休在“教职员工休息室”吃饭,和同样做候补的一个男老师比邻而坐,我们聊了一会儿,期间他多次用“survive”这个词形容他的每一天,我当时还觉得这个老师的态度太“消极”:教师职业是高尚的、受人尊敬的,教师本为人表率,是班级的核心,应该时时做到热情高涨、充满活力,这样才能鼓舞和提高学生的“斗志”嘛,如果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,安全打发每一天,那老师不就失去了为人师表的意义?
想当初我刚从加国学院毕业,就被我们本地的机构聘为教师,虽说是候补,可当时几乎人人都从候补开始,校长也不例外。而且看当时的情形,整个学院好像就我这么一个中国人,越发激发了我对新工作高涨的热情。我拉了一个单子,上面写满我预备自修的科目和项目,准备洋洋洒洒地走上我的教师之路。
可是不久,我的热情就受了挫:本以为我的数学还行,可第一次去教书,就遭遇了12年级的“统计学”这个大难题;本该教science(科学)吧,可它又分理化生和地球天文等,虽说教材不深,可谁都知道,这教学一向都是“要想拿出一碗水,自己先得有一桶水”才行,光凭我在仓促之中自学几本书就去挥洒自如实有些勉强。
虽说遇到法语和音乐这样的offer, 我一律自知之明地回答“no”, 可遇到了体育或者“实用技术”这样的活,为了生计,有时候也接。遇到以上这些情况,结果就可想而知了:侃侃而谈自然是不成了,能从那一堂堂课上“存活”下来就不错了。这时候我才理解了那个男老师的语重心长的话。
开始我对学校这种做法很有情绪:试问哪一个老师不是只有一两个“专业”?又有谁能做到专业的“全能”?别说我们这些“半路出家”的移民,就算本地人,本地生本地长本地受的教育,也很难有几个文理全通的“通才”啊。可后来一想,这可不就是“候补”的意义吗?哪里需要哪里去。
再说不管是学校还是代课老师,都很清楚“候补”老师的苦衷,对我们的要求也不能太高。
当然我这些专业不专业的讨论,是针对高中而言的,至于小学,没得商量,十八般武艺,还真得样样精通。起初我也发过怵,觉得我这没有北美教育背景的人,样样都得学样样都得补,就怕来不及。可代了一年多课后,我发现其实教学是要讲“方法学”的,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未必就是一个好老师,而一个态度认真、精通“教学法”的普通人通过不断学习,总结经验,倒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教师。
这其中的道理,非亲身体会是不能理解其中奥妙的。总之现在让我去教小学,不管什么年级什么科目,我按“教委”的要求,至少提前十五分钟到代课学校,仔细翻看代课老师留下的教案,十五分钟后就可以走上讲台挥洒自如了。
当然我这不是说,小学代课就没有一点儿困难了。其实不然,有些老师(比如我自己)就宁愿代高中不愿代小学,原因是高中代课,三堂课就算一个全天的工作量,三堂课加起来也就是两个半小时,就算加上其他巡视饭厅、图书馆或者走廊等这种额外的“执勤”任务,也就是三个多小时;而小学,从进校门到出校门,七个多小时都要和学生寸步不离,教学都是小菜,重要的是管理学生的吃喝拉撒和安全等等。
有一次代的是幼儿园,只见这一班二十多个“洋娃娃”,个个如小天使,可也个个是顽皮至极的天使,对这一群小家伙,凶又凶不得,讲道理又不听,只好一个个地哄。刚刚安抚了杰克,小萨拉又哭了,刚刚哄好了小萨拉,安娜又在叫了……正忙着,小卢克过来说:“老师我要撒尿”还没等说完,我们俩人都已经站在一汪“水地“里了。
像这样的插曲,经常碰到,有苦有乐。用我一个同为候补老师“战友” 的话说:“做候补教师这行当的,很少有完美的时候”。
 加拿大多伦多新飞扬留学
加拿大多伦多新飞扬留学